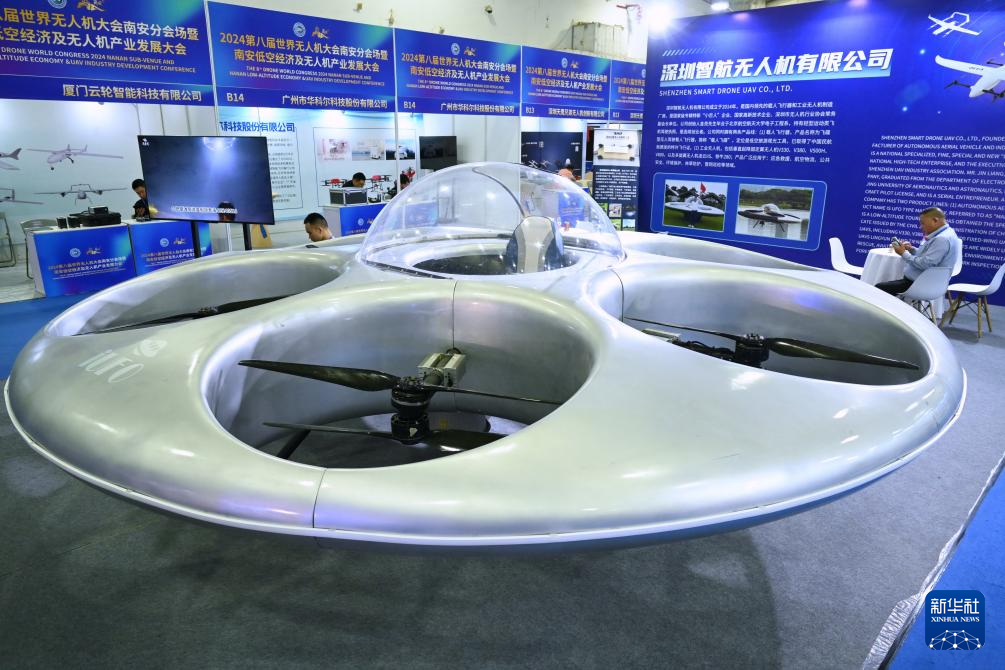汗青贊美把人們引向逝世亡的疆場,卻不屑于講述使人們賴以保存的農田;汗青明白了解天子私生子的名字,卻不克不及告知我們小麥是從哪里來的。
——[法]法布爾
小麥原產瑜伽教室于西亞的肥饒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考古證據顯示,它在距今年夜約4500-4000年前經由過程歐亞草原通道與綠洲通道兩條分歧途徑傳進中國際地。年齡時代就已被人們視作“五谷”之一,唐代中后期的兩稅法已將其作為正式征稅對象,它在漫長的外鄉化經過歷程中逐步代替了南方地域的黍與粟,成為最勝利的外來作物,并塑造了中國“南稻北麥”的農業生孩子格式。但其外鄉化過程也并非是好事多磨的,它在裁減外鄉農作物的同時,也碰到諸多來自天氣、飲食等方面的妨礙,本身也在不竭地被改革,以順應外鄉化的需求。
一、天氣、地勢前提與小麥蒔植技巧之演進
小麥是一種秋播、夏收的作物,其位于西亞的原產地為地中海天氣,該地冬春季溫順多雨、夏日干旱少雨,這既知足了小麥發展期對水分的需求,又避開了夏日干旱的要挾,同時夏日干燥的天氣也為小麥的收獲供給了傑出的前提。而東亞地域則屬于季風尚候,冬春缺雨,晦氣于小麥的發展,同時夏日頻仍的降雨也晦氣于小麥的成熟與收獲,故而考古學家趙志軍以為,在距今 7000 年擺佈,小麥就曾經傳佈到了中亞地域的東北部,但卻在此地皮桓數千年后才持續向東進進東亞,招致小麥東傳速率變緩的緣由就是兩地天氣的分歧。
進進華夏地域后,干旱的天氣仍然制約著小麥的發展,而該地原產主糧作物粟的需水量僅為小麥的二分之一,故而在食糧作物中,粟被視作“五谷之長”,小麥在前人所謂的“五谷”“六谷”“八谷”“九谷”中都排在靠后的地位,僅僅由於它的收獲季候是往年粟、黍庫存正要耗盡而秋糧尚未成熟的夏日,能起到繼盡續乏的感化,所以被農夫視作是傳統主糧作物粟的一種彌補。西漢董仲舒曰:“《年齡》他谷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圣人于五谷最重麥與禾也”,現實并不是對彼時小麥蒔植普遍性的表述,僅是由於它在繼盡續乏方面所起的感化,故而見載于史乘。
年齡時代,小麥的主產區在西方的齊魯,即《范子計然》所謂的“西方多麥”,且彼時的小麥基礎發展在接近水源的河濱,如齊國境內的濟水,就有“濟水通和而宜麥”的記錄。戰國時代,跟著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的興修,農人開端引河水溉田,農田澆灌前提獲得改良,小麥主產區開端向黃河中游擴大。秦漢時代,尤其是漢武帝時代,當局屢次興建水利,在關中先后開鑿了龍首渠、六輔渠、白渠、靈軹渠、成國渠、渠等年夜型水利工程,至于其他小渠與陂山通道更是不成勝計,這些水利工程年夜年夜改良了農田的澆灌前提,使很多雨養田釀成水澆地,為小麥蒔植向西擴大供給了傑出前提。漢武帝曾親身下詔號令關中蒼生蒔植冬小麥(宿麥),漢成帝時,當局也曾調派農學家氾勝之“教田三輔”,史載“昔漢遣輕私密空間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但水利工程的建築究竟只能顧及無限之區域,在間隔河渠較遠的地步上,小麥仍是由於缺水而難以蒔植。西漢農學家氾勝之謹嚴地提出農人在種麥時,要以酸漿水浸蠶糞來薄漬麥種,并在天未亮之前趕緊收穫,以使得種子和露珠一路下到田里。而在冬全國雪之后,亦要“以物輒藺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往”,來對麥田停止保墑。直到北朝時代,小麥還多被蒔1對1教學植在低洼的“下田”中,彼時平易近歌里還唱道:“高田種小麥,稴穇不成穗。男兒在異鄉,那得不憔悴?”可見泥土墑情缺乏還是制約小麥進一個步驟推行的主要原因。
年夜約與此同時,情形也在漸漸產生著轉變。此時南方地域構成了一整套節水保墑的農業辦法,即所謂的“耕-耙-耱”三位一體的旱地耕耘技巧系統,在原有“深耕熟耘”與“耕”“耱”的基本上加上“耙”,耕地后,先用畜力耙(賈思勰稱為鐵齒楱)將土塊耙碎,然后再用耱摩平,一方面經由過程深耕進步了泥土的吸水才能,另一方面經由過程“耙”“耱”堵截了泥土的毛細管,削減蒸爆發用,堅持泥土中水分的殘留。這些技巧皆被用于小麥的蒔植中,賈思勰提到:“凡麥田,常以蒲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這套技巧的完美進步了作物的抗旱保墑才能,為小麥蒔植的進一個步驟擴大奠基了堅實的技巧基本。迨至唐建中元年(780)開端履行兩稅法,分夏、秋兩季征收,已明白將之前被視為“雜稼”的小麥列進正式征稅對象,標志著小麥已上升到與粟劃一主要的位置。南方地域粟麥易位的正確時光似乎并未有確實的節點,但這個經過歷程應當產生在宋明之間。依據宋應星《天工開物》的記錄,明代后期,僅小麥一項曾經占那時南方地域大眾口糧的對折之多,而剩下一半則由粟與黍、稻、粱等雜糧共享,可見中國的農業生孩子格式已由傳統的“南稻北粟”過渡到“南稻北麥”。明清時代,小麥的普遍蒔植推進了井灌技巧的成長,而彼時南方地域井灌技巧的分散與普及,也是小麥更進一個步驟擴大之證據。乾隆年間黃可潤的《畿輔見聞錄》中記錄那時畿輔地域的農人:“近河者資河,無河者開井,則磽確外無不成麥之地,無不愿種麥之平易近”。
淮河以南的南邊地域由于地勢低洼、潮濕多雨,并不適于小麥的發展,所以小麥在南邊的蒔植較之南方要晚很多,且是在南方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東晉年夜興元年(318)當局在徐、揚二州督種小麥,這是江南地域最早的麥作記載。唐宋時代,跟著安史之亂與靖康之難帶來的生齒活動,大批南方報酬迴避戰亂遷居南邊,麥作亦隨之傳進,特殊是隨同著宋室南遷,小麥在南邊的蒔植更是到達了飛騰,史稱“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閩、廣,東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于種稻。而耕戶輸租,只要秋課,而種麥之利,獨回客戶。于是競種春稼,縱目不減淮北。”南邊地域底本以稻作農業為主,麥作的傳進使得一些不合適種水稻的丘陵、高田獲得開闢,擴展了地盤應用的范圍,所以處所官在勸農時經常請求農人“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播麥”,“燥處宜麥,濕處宜禾”。同時,跟著麥作的進一個步驟成長,呈現了稻麥復種的二熟制。今朝,有關于稻麥復種制的最明白的記錄首見于唐代云南地域,長江中下流地域的稻麥復種則始見于南宋陳旉的《農書》。稻田種麥的最年夜障礙原因是稻地步勢低洼,假如泥土不顛末充足排水,小麥就會長勢欠安。當稻麥復種呈現之后,人們起首采用“耕治曬暴”的方式來排干稻田中的水分,再種上小麥,完成稻麥的復種。后來又呈現了“開溝作疄”的稻田整地技巧,元代王禎具體描寫了其經過歷程:在水稻收獲后整地曝曬,然后用犁來對農田停止起壟,兩個相鄰的高壟之間為畎溝,一段耕完后用鋤頭將高壟截斷,開成泄水通道,如許水就不會在田里積累或滯留,將小麥種于壟上。這種技巧大要在唐朝時就已有雛形,杜甫的詩中就有“山田麥無壟”的描寫,由於山地步勢高,無需作壟,也正面反應了彼時平原種麥時應有壟溝。開溝作疄技巧的構成與普及對小麥在南邊的擴大起到了至關主要的感化,以致于南宋時代的溫州已是“彌川布壟,其苗幪幪,無不種麥矣”。
我國年夜部門地域因受季風的影響,夏日廣泛多雨,而此時正值小麥的收獲時代,風雨侵襲常常招致小麥收獲時倒伏與落粒損耗,形成嚴重喪失,故而平易近間有“收麥如救火”的諺語,進步收麥速率也就成為小麥普及推行中的一個要害原因。為此,金元時代的農書《韓氏直說》提出“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的措施。人們還從改良收割東西進手來進步收割效力,元代南方麥區已廣泛采用了麥釤、麥綽和麥籠配套的麥出工具,“一日可收十余畝”,據稱相較于鐮刀收割,進步了十倍的效力。對于那些因被風雨催倒而不克不及用麥釤來收割的倒伏小麥,王禎提出應用抄竿來抄起倒伏莖穗,另一人則共同以麥釤收割。收割完的小麥在脫粒之前,為防止被雨水淋濕,要用積苫來籠罩。《王禎農書·農器圖譜》中專辟“麰麥門”一章,對這些麥作耕具加以推行宣揚。
二、食用、加工方法與小麥飲食不雅念的變遷
在人類汗青的初期,谷物是被放在石板上烤熟的,后來逐步發現了“蒸谷為飯,烹谷為粥”的蒸煮食用方法,但非論以何種方式烹制,黍、粟、稻甚至菽等谷物皆是采用粒食的方法來食用。受此影響,小麥自西亞傳進我國之后,最後也被用以粒食,即整粒蒸煮或磨成碎粒麥屑“合皮而炊之”,這種食物被稱作“麥飯”。由于小麥的麩皮很厚,使得它粒食的可口感很差,在很長時光內麥飯被人們視作“野人農民之食”,在飲食上最基礎不具有與光滑可口的小米、年夜米相對抗的才能。周立剛依據華夏地域年齡戰國時代遺址里人骨的穩固同位素剖析,以為彼時貴族多以粟為主糧,而位置較低的人或殉人則大批食用小麥,也印證了以上不雅點。
戰國早期至秦漢時代,中國自力發現了轉磨,考古學家以為,依據其進料口部位與雙磨眼的構造剖析極有能夠是為了小麥的精加工而design,即小麥制粉的需求催生了轉磨技巧的發現。石磨技巧的呈現使得小麥的食用方法由粗糲的粒食變為精致的粉食,它在漢代獲得了必定水平之推行,那時的貴族多喜面食。據記錄,東漢時代,“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依據《釋名》的記錄,那時的面食品種有胡餅、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此中的湯餅,應是晚期的面片或面條,此中的蒸餅,應是用發面制作的面食。西晉束晳所作《餅賦》中呈現了“㬅頭”,辛德勇傳授以為即為饅頭的古寫法。彼時的面粉發酵技巧已甚為成熟,《齊平易近要術》就記錄了以酸漿與粳米來制作“餅酵”的方式,依據賈思勰的論述,其技巧起源于成書時光更早的《食經》。但由于面粉加產業的滯后與壟斷,那時的面粉仍是比擬稀疏且珍貴,面食也多為貧賤人家所專享,貧民仍以麥飯為食。
唐代是面食的周全普實時期,那時對交際流頻仍,西域的胡人攜帶各色胡食進進華夏,此中最重要的就有胡餅、燒餅、畢羅、搭納等面食,跟著社會經濟的連續繁華,胡食成為了全部社會的一種飲食時髦。各地均有售賣胡餅的餅肆,白居易從長安被貶官到四川忠州后,發明本地亦有賣胡餅的小店,便買了一些寄給友人,讓他品鑒與長安城輔興坊所做能否滋味雷同。那時長安城里還有專賣畢羅的店展,布衣蒼生皆往買食,而一些窮進士也“多會于酒樓食畢羅”,可見那時面食曾經在通俗大眾間風行開來。宋代以降,面食更為廣泛且品種日趨多樣。《夢華錄》記錄了北宋首都東京(即開封)的各色餅店,分為油餅店、胡餅店兩類,這些店舖自天尚未亮的五更起便生意興隆,那時武成王廟前的張家餅店與黃建院前的鄭家餅店,“每家有五十余爐”,用來烤制胡餅。《夢粱錄》記錄了南宋時杭州的面食店,各色面點包羅萬象,饅頭有四色饅頭、生餡饅頭、正色煎花饅甲等,包子有細餡年夜包子、水晶包兒、筍肉包兒、蝦魚包兒、江魚包兒、蟹肉包兒等,面條有年夜片展羊面、三鮮面、炒鱔面等……成書于元天歷三年(1330)的《飲膳正要》中呈現了“掛面”,顛末晾曬與風干,使得面食變得更易貯存,進一個步驟加快了面食的傳佈。
唐宋時代,跟著小麥在南邊地域蒔植的鼓起,關于小麥有毒的談吐開端呈現,人們以為南邊的小麥由于生于干冷的周遭的狀況,故而有毒,食用會惹起“病狂”。前人對此停止過說明,以為南方的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全備四時之氣,故無毒”,而南邊的小麥冬種夏熟,只經過的事況了冬、春、夏三個季候,少了一氣,故而有毒。筆者以為,所謂的“麥毒”能夠是由以下兩個原因惹起的。起首,那時文獻皆記錄南邊生產的小麥有毒,而南方卻從無記錄,能夠是由於在天氣潮濕的南邊,小麥不難得赤霉病,人們食用了患病小麥磨制的粉,故而惹起急性中毒。明嘉靖《永春縣志》的撰者對此景象舞蹈場地有過猜測,他以為“北麥粒小而堅,面多;南麥粒年夜而松,面少。北人任南都不食南面,云飽脹難消,蓋有毒也”,而出粉率變低恰是小麥患赤霉病的一個表示。其次,小麥種皮較薄,組織構造疏松,吸濕才能較強。故而小麥蘊藏應特殊留意防潮,應充足應用小麥收獲后的夏日低溫前提停止暴曬,再行進庫,進庫后亦要做好防潮辦法。而南邊地域天氣干冷,晦氣于小麥的曝曬,明代烏程人王濟往廣西橫州仕進,發明本地似“不知種麥之法”,經訊問才得知,該地之前也種過小麥,但“遇熟時,不伺曝干即鞭凈貯之器間,彼土又多干冷,皆黰為紅玄色。食皆無味,或有食即吐逆成疾”。于是他撰寫了麥的蒔植與加入我的最愛之法,張貼于各村墟,才“間亦有人種矣”。清咸豐《長汀縣志》的編輯者也以為,“曬燥”是防止麥毒的主要辦法之一。而前人記錄麥毒的內在表示是“面有熱毒者,為多是陳黦之色”,即其色彩特征為陳腐的黃玄色,正與上文中的“黰為紅玄色”相符,這些潮腐的小麥被人們食用后,便會招致吐逆等病癥的產生,繼而誤以為小麥自己有毒。
小麥的食用方法決議著人們對小麥種類的選擇,在其傳進的晚期,小麥以粒食為主,故而人們多選擇易于蒸煮的小麥種類來蒔植,一旦粉食成為主流后,這些小麥種類就變得不勝用,如唐代云南地域,“其小麥面軟泥少味”,南宋時代,“陜西沿邊地苦冷,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成食,如熙州斤面,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另一方面,中式面點饅頭、包子、餃子等皆是應用中筋面粉來制作,這也影響了國人對小麥種類的選擇,如《齊平易近要術》里就提到一種名為“山提小麥”的精良種類,其性黏軟,被當做貢品供獻給天子。而東方國度則重要用小麥來烤制面包,這就需求強筋小麥粉,故而其日常選種與小麥育種研發的重點皆是高筋小麥,而我國的優質高筋小麥則略出缺口,仍需入口,這也與飲食習氣相干。對于這種差別,農史學家曾雄生精辟地總結道:“我們接收了小麥,但沒有選擇面包”。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在其《中國伊朗編》中高度稱贊中國人歷來樂于接收外來作物,以為其“采納很多有效的本國植物認為己用,并把它們并進本身完全的農業體系中往。”可以說,小麥是此中最為杰出的代表。我國有著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史,與其他后來傳進的外來作物分歧,從某種水平下去說,小麥是與中漢文明一路生長起來的。殷商時代的甲骨文里就有很多“告麥”“受麥”與“登麥”的記錄;年齡時代,可否對的識別麥曾經成為鑒定一小我智商正常與否的一項標志;前人于麥收時要向祖先供奉嘗新,而以齊魯年夜地為代表的諸多地域至今還聚會場地保存著給已故親人上新麥墳的風俗;芃芃的麥苗與金黃色的麥田也成為歷代詩人詠頌的對象……小麥在逐步被歸入中國傳統農業系統的同時,也在必定水平上介入塑造著中漢文明。